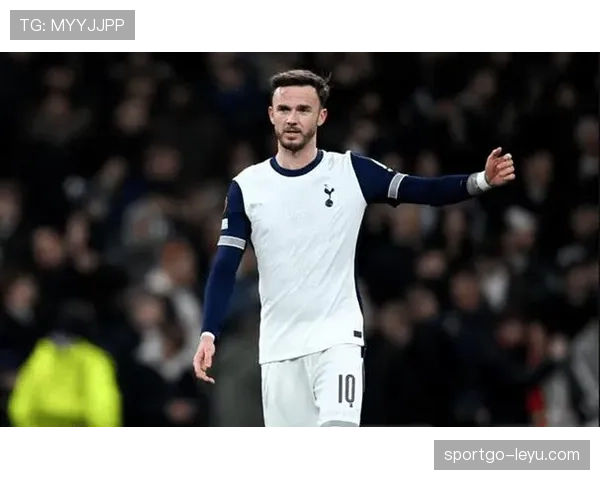зәҪдјҰе Ўе®ЎеҲӨеҶҚе®Ўи§ҶпјҡеҺҶеҸІй•ңйүҙдёӯзҡ„жі•еҫӢдёҺйҒ“еҫ·д№ӢжҖқ
еәҹеўҹдёӯзҡ„жі•еәӯ
1945е№ҙ11жңҲ20ж—ҘпјҢеҫ·еӣҪзәҪдјҰе ЎеҸёжі•е®«600еҸ·е®ЎеҲӨеәӯеҶ…пјҢеҜ’ж„Ҹжё—е…ҘзҹіеўҷгҖӮиҝҷеә§жӣҫи§ҒиҜҒзәізІ№е…ҡд»ЈдјҡзӢӮзғӯзҡ„еҹҺеёӮпјҢеҰӮд»ҠжҲҗдёәжё…з®—жҲҳдәүзҪӘиЎҢзҡ„иө·зӮ№гҖӮеҚҒдәҢеҗҚзӣҹеӣҪжі•е®ҳз«Ҝеқҗй«ҳеҸ°пјҢдёӢж–№иў«е‘ҠеёӯдёҠпјҢжҲҲжһ—гҖҒиө«ж–ҜгҖҒйҮҢе®ҫзү№жҙӣз”«зӯүдәҢеҚҒдёҖеҗҚзәізІ№й«ҳеұӮзҘһжғ…еҗ„ејӮвҖ”вҖ”жңүдәәеӮІж…ўпјҢжңүдәәжғ¶жҒҗпјҢж— дәәиғҪйҖғиҝҮеҺҶеҸІзҡ„еҮқи§ҶгҖӮзӘ—еӨ–пјҢеҹҺеёӮд»ҚеңЁз“Ұз ҫдёӯе–ҳжҒҜпјҢиҖҢдәәзұ»йҰ–ж¬Ўе°қиҜ•д»Ҙжі•еҫӢиҖҢйқһеӨҚд»Үзҡ„ж–№ејҸе®ЎеҲӨеӣҪ家зҪӘиЎҢгҖӮ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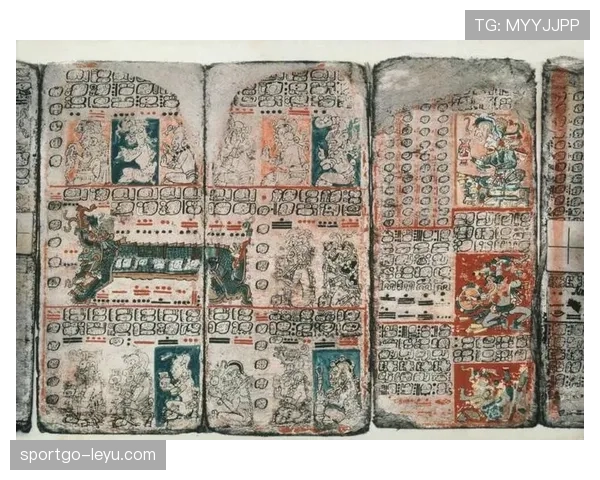
иҝҷеңәе®ЎеҲӨ并йқһйў„и®ҫз»“еұҖзҡ„иЎЁжј”гҖӮе°Ҫз®ЎзәізІ№жҡҙиЎҢе·Іе№ҝдёәдәәзҹҘпјҢдҪҶеҰӮдҪ•еңЁжі•еҫӢжЎҶжһ¶еҶ…е®ҡзҪӘпјҹдҫөз•ҘжҲҳдәүжҳҜеҗҰжһ„жҲҗзҠҜзҪӘпјҹдёӘдәәиғҪеҗҰд»ҘвҖңжңҚд»Һе‘Ҫд»ӨвҖқдёәз”ұе…ҚиҙЈпјҹиҝҷдәӣй—®йўҳеңЁеҪ“ж—¶е№¶ж— е…ҲдҫӢгҖӮзҫҺеӣҪйҰ–еёӯжЈҖеҜҹе®ҳзҪ—дјҜзү№В·жқ°е…ӢйҖҠеқҡжҢҒпјҡвҖңжҲ‘们дёҚжҳҜеңЁеӨҚд»ҮпјҢиҖҢжҳҜеңЁзЎ®з«ӢдёҖз§Қи®©жңӘжқҘжҲҳдәүеҸ‘еҠЁиҖ…з•Ҹжғ§зҡ„规еҲҷгҖӮвҖқ
еӣҪйҷ…еҶӣдәӢжі•еәӯпјҲIMTпјүзҡ„и®ҫз«Ӣжң¬иә«еҚіжҳҜдёҖж¬ЎеҲ¶еәҰеҶ’йҷ©гҖӮе®ғиһҚеҗҲдәҶиӢұзҫҺжі•зі»зҡ„еҜ№жҠ—еҲ¶дёҺеӨ§йҷҶжі•зі»зҡ„зә й—®еҲ¶пјҢе…Ғи®ёиў«е‘ҠиҒҳиҜ·еҫӢеёҲгҖҒиҙЁиҜҒиҜҒжҚ®пјҢз”ҡиҮідј е”Өе·ұж–№иҜҒдәәгҖӮиҝҷз§ҚзЁӢеәҸжӯЈд№үзҡ„еқҡжҢҒпјҢеңЁе°ёеұұиЎҖжө·зҡ„иғҢжҷҜдёӢжҳҫеҫ—иҝ‘д№ҺеҘўдҫҲпјҢеҚҙжҒ°жҒ°еҘ е®ҡдәҶзҺ°д»ЈеӣҪйҷ…еҲ‘жі•зҡ„еҹәзҹігҖӮ
жі•еҫӢдёҺйҒ“еҫ·зҡ„жӢүй”Ҝ
е®ЎеҲӨиҝҮзЁӢдёӯпјҢжңҖжҝҖзғҲзҡ„дәӨй”Ӣ并йқһжқҘиҮӘиҜҒжҚ®пјҢиҖҢжҳҜжі•зҗҶж №еҹәгҖӮеҫ·еӣҪиҫ©жҠӨеҫӢеёҲиҙЁз–‘пјҡиө·иҜүвҖңз ҙеқҸе’Ңе№ізҪӘвҖқиҝқеҸҚвҖңжі•ж— жҳҺж–ҮдёҚдёәзҪӘвҖқеҺҹеҲҷвҖ”вҖ”жҜ•з«ҹ1939е№ҙеүҚпјҢеӣҪйҷ…法并жңӘжҳҺзЎ®е°ҶеҸ‘еҠЁдҫөз•ҘжҲҳдәүе®ҡдёәдёӘдәәеҲ‘дәӢиҙЈд»»гҖӮиӢҸиҒ”жі•е®ҳе°јеҹәзҗҙ科еҲҷеҸҚй©іпјҡвҖңеҰӮжһңзӯүеҫ…жі•еҫӢжқЎж–ҮеҶҷе°ұжүҚиЎҢеҠЁпјҢдәәзұ»е°Ҷж°ёиҝңж— жі•йҳ»жӯўдёӢдёҖеңәжө©еҠ«гҖӮвҖқ
йҒ“еҫ·зӣҙи§үдёҺжі•еҫӢеҪўејҸдё»д№үеңЁжӯӨжҝҖзғҲзў°ж’һгҖӮжЈҖж–№еҮәзӨәдәҶйӣҶдёӯиҗҘи§Јж”ҫж—¶зҡ„еҪұеғҸпјҡе Ҷз§ҜеҰӮеұұзҡ„е°ёдҪ“гҖҒйӘЁзҳҰеҰӮжҹҙзҡ„е№ёеӯҳиҖ…гҖҒжҜ’ж°”е®Өзҡ„ж“ҚдҪңи®°еҪ•гҖӮиҝҷдәӣиҜҒжҚ®йңҮж’јдё–з•ҢпјҢеҚҙйҡҫд»ҘзӣҙжҺҘеҜ№еә”дј з»ҹеҲ‘жі•жқЎж¬ҫгҖӮжңҖз»ҲпјҢжі•еәӯеҲӣйҖ жҖ§ең°жҸҙеј•гҖҠдјҰж•Ұе®Әз« гҖӢ第6жқЎпјҢе°ҶвҖңеҚұе®ідәәзұ»зҪӘвҖқзәіе…Ҙз®Ўиҫ–вҖ”вҖ”иҝҷдёҖжҰӮеҝөжӯӨеүҚд»…еӯҳеңЁдәҺеӯҰиҖ…и®әиҝ°дёӯгҖӮ
дәүи®®йҡҸд№ӢиҖҢжқҘгҖӮжү№иҜ„иҖ…з§°е…¶дёәвҖңиғңеҲ©иҖ…зҡ„жӯЈд№үвҖқпјҢе°Өе…¶еҪ“иӢҸиҒ”иҮӘиә«еңЁеҚЎе»·жЈ®жһ—дәӢ件дёӯзҡ„и§’иүІиў«еҲ»ж„ҸеӣһйҒҝж—¶гҖӮдҪҶж”ҜжҢҒиҖ…жҢҮеҮәпјҢиӢҘеӣ зЁӢеәҸз‘•з–өж”ҫејғе®ЎеҲӨпјҢзӯүдәҺзәөе®№жҡҙиЎҢйҖҚйҒҘжі•еӨ–гҖӮжӯЈеҰӮжі•е®ҳеҠідјҰж–ҜжүҖиЁҖпјҡвҖңе®ҢзҫҺжӯЈд№үиҷҪдёҚеҸҜеҫ—пјҢдҪҶжңүзјәйҷ·зҡ„жӯЈд№үиҝңиғңдәҺж— жӯЈд№үгҖӮвҖқ
еҲӨеҶідёҺйҒ—дә§
1946е№ҙ10жңҲ1ж—ҘпјҢеҲӨеҶід№Ұй•ҝиҫҫ250йЎөгҖӮеҚҒдәҢдәәеҲӨеӨ„з»һеҲ‘пјҢдёүдәәз»Ҳиә«зӣ‘зҰҒпјҢеӣӣдәәжңүжңҹеҫ’еҲ‘пјҢдёүдәәж— зҪӘйҮҠж”ҫгҖӮжҲҲжһ—еңЁиЎҢеҲ‘еүҚеӨңжңҚжҜ’иҮӘе°ҪпјҢз•ҷдёӢжңӘе®ҢжҲҗзҡ„еҝҸжӮ”гҖӮеҖјеҫ—жіЁж„Ҹзҡ„жҳҜпјҢжі•еәӯжҳҺзЎ®жӢ’з»қвҖңйӣҶдҪ“зҪӘиҙЈвҖқйҖ»иҫ‘вҖ”вҖ”д»…иҝҪ究дёӘдәәиҙЈд»»пјҢйҒҝе…Қе°Ҷж•ҙдёӘеҫ·ж„Ҹеҝ—ж°‘ж—Ҹй’үдёҠиҖ»иҫұжҹұгҖӮ
зәҪдјҰе Ўзҡ„зңҹжӯЈйҒ—дә§дёҚеңЁз»һзҙўпјҢиҖҢеңЁж–Үжң¬гҖӮе…¶зЎ®з«Ӣзҡ„дёғйЎ№еҺҹеҲҷвҖ”вҖ”еҢ…жӢ¬дёӘдәәеҜ№еӣҪйҷ…жі•д№үеҠЎзҡ„зӣҙжҺҘжүҝжӢ…гҖҒе®ҳиҒҢдёҚиғҪиұҒе…ҚзҪӘиҙЈзӯүвҖ”вҖ”иў«иҒ”еҗҲеӣҪеӨ§дјҡдәҺ1947е№ҙе…ЁзҘЁйҖҡиҝҮпјҢжҲҗдёәеӣҪйҷ…еҲ‘жі•зҡ„вҖңй»„йҮ‘еҮҶеҲҷвҖқгҖӮ1998е№ҙгҖҠзҪ—马规зәҰгҖӢеҲӣз«ӢеӣҪйҷ…еҲ‘дәӢжі•йҷўж—¶пјҢзәҪдјҰе ЎеҺҹеҲҷиў«е…Ёж–ҮеҗёзәігҖӮ
жӣҙж·ұиҝңзҡ„еҪұе“ҚеңЁдәҺи§Ӯеҝөйқ©е‘ҪгҖӮжӯӨеүҚпјҢжҲҳдәүиў«и§ҶдёәеӣҪ家иЎҢдёәпјҢе°ҶйўҶдёҺж”ҝе®ўдә«жңүиұҒе…ҚпјӣжӯӨеҗҺпјҢжҢҮжҢҘе®ҳиӢҘзәөе®№жҡҙиЎҢпјҢе°ҶйқўдёҙдёӘдәәиҝҪиҜүгҖӮиҝҷдёҖзҗҶеҝөеңЁеҚўж—әиҫҫгҖҒеүҚеҚ—ж–ҜжӢүеӨ«й—®йўҳеӣҪйҷ…еҲ‘дәӢжі•еәӯдёӯеҸҚеӨҚйӘҢиҜҒпјҢзӣҙиҮід»Ҡж—Ҙжө·зүҷзҡ„жЈҖеҜҹе®ҳд»ҚжүӢжҢҒзәҪдјҰе ЎеҲӨдҫӢдҪңдёәжӯҰеҷЁгҖӮ
й•ңйүҙдёҺеӣһе“Қ
дёғеҚҒдҪҷе№ҙеҗҺпјҢзәҪдјҰе Ўзҡ„е№ҪзҒөд»ҚеңЁе…ЁзҗғжёёиҚЎгҖӮеҪ“еҸҷеҲ©дәҡеҢ–жӯҰиўӯеҮ»гҖҒзј…з”ёзҪ—е…ҙдәҡеҚұжңәжҲ–д№Ңе…Ӣе…°еёғжҒ°дәӢ件еҸ‘з”ҹж—¶пјҢеӣҪйҷ…зӨҫдјҡзҡ„第дёҖеҸҚеә”дёҚеҶҚжҳҜжІүй»ҳпјҢиҖҢжҳҜиҝҪй—®пјҡвҖңи°ҒиҜҘиҙҹиҙЈпјҹиҜҒжҚ®дҪ•еңЁпјҹиғҪеҗҰиө·иҜүпјҹвҖқиҝҷз§ҚжҖқз»ҙиҪ¬еҸҳпјҢжӯЈжҳҜзәҪдјҰе Ўж’ӯдёӢзҡ„з§ҚеӯҗгҖӮ
然иҖҢжҢ‘жҲҳд»ҺжңӘж¶ҲеӨұгҖӮеӨ§еӣҪж”ҝжІ»еёёдҪҝеӣҪйҷ…еҸёжі•жӯҘеұҘз»ҙиү°вҖ”вҖ”зҫҺеӣҪжңӘеҠ е…ҘеӣҪйҷ…еҲ‘дәӢжі•йҷўпјҢдҝ„зҪ—ж–ҜеҗҰеҶіе®үзҗҶдјҡ移дәӨеҸҷеҲ©дәҡжЎҲ件пјҢйқһжҙІеӣҪ家жҠұжҖЁйҖүжӢ©жҖ§еҸёжі•гҖӮзәҪдјҰе Ўзҡ„еұҖйҷҗжҖ§еңЁжӯӨжҳҫзҺ°пјҡжІЎжңүејәеҲ¶жү§иЎҢеҠӣзҡ„жі•еҫӢпјҢз»Ҳ究и„ҶејұгҖӮ
дҪҶе®ғзҡ„ж ёеҝғеҗҜзӨәеҺҶд№…ејҘж–°пјҡйқўеҜ№зі»з»ҹжҖ§жҡҙиЎҢпјҢдәәзұ»еҝ…йЎ»и¶…и¶ҠвҖңд»ҘзңјиҝҳзңјвҖқзҡ„еҺҹе§ӢйҖ»иҫ‘пјҢжһ„е»әеҸҜйў„жңҹзҡ„规еҲҷгҖӮжӯЈеҰӮжЈҖеҜҹе®ҳжқ°е…ӢйҖҠеңЁејҖеәӯйҷҲиҜҚдёӯжүҖleyu乐鱼иӯҰзӨәпјҡвҖңжҲ‘们жҜ«дёҚжҖҖз–‘иў«е‘Ҡзҡ„зҪӘиЎҢпјҢдҪҶиӢҘеӣ жӯӨж”ҫејғжӯЈеҪ“зЁӢеәҸпјҢжҲ‘们е°ҶдәІжүӢеҹӢ葬иҮӘе·ұиҜ•еӣҫжӢҜж•‘зҡ„ж–ҮжҳҺгҖӮвҖқ
д»ҠеӨ©йҮҚе®ЎзәҪдјҰе ЎпјҢдёҚжҳҜдёәдәҶеӨҚеҲ»дёҖеңәеҺҶеҸІе®ЎеҲӨпјҢиҖҢжҳҜзЎ®и®ӨдёҖдёӘдҝЎеҝөвҖ”вҖ”еҚідҪҝеңЁиҮіжҡ—ж—¶еҲ»пјҢжі•еҫӢд»ҚеҸҜжҲҗдёәеҲәз ҙй»‘жҡ—зҡ„еҫ®е…үгҖӮиҝҷжқҹе…үжҲ–и®ёж‘ҮжӣіпјҢеҚҙи¶ід»Ҙз…§дә®еҗҺжқҘиҖ…еүҚиЎҢзҡ„и·ҜгҖӮ